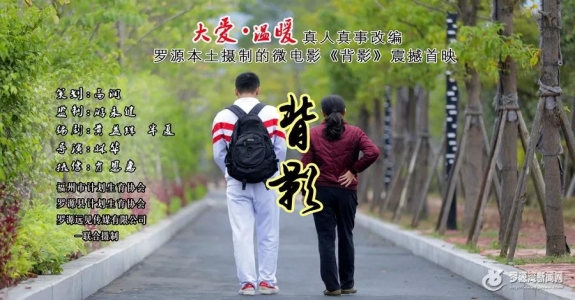恐婚时代:18个媒人说一门亲 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http://www.lywxww.com 2014-03-24 08:53:42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 大 中 小】

剧中父母为了给未来儿媳凑够三斤百元面值人民币的彩礼而将钱用水浸湿。这来自时下冀南农村一些地方索要“新三金”彩礼的现实。《恐婚时代2》剧照
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事,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冀南农村青年婚恋现状调查
有2000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22~26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30人;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2000人,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30多人……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却寥寥无几。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邯郸曲周、鸡泽、广平、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找媳妇难”已成为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
曲周县李于子口一位40多岁的热心妇女告诉记者,临近各村以至临近各县都是如此——这两年每个村都有20多个找不着对象的小伙子,“条件还都不差”。
冀南农村普遍出现的“找媳妇难”,已不仅仅是让父母和本人头疼的“家务事”。
有鸡泽县赵庄村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开会就为这事发愁!”而当一位鸡泽县的妇女向曲周县的朋友打听是否有适龄姑娘的信息时,这位朋友立刻笑着“警告”她:“你可不能挖我们村的墙角啊!”
有媒体报道,隆尧县更有村委会向所有村民承诺:只要把女儿嫁到本村,奖励2000元;只要把本村或外村的女青年介绍给本村的男青年,奖励介绍人1000元。
记者发现,由于“找媳妇难”引发的专业媒人“不择手段”谋利、女方对彩礼“狮子大张口”,以及暴露出来的农村传统婚恋观念令人堪忧。
四五个小伙子排着队跟同一个姑娘相亲
“19岁时,对于相亲找对象,感觉就和看偶像剧一样——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女神’。” 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87年出生的他“相亲史”始于19岁。
后来由于20岁外出打工,婚姻大事被暂时“搁下”。3年前,24岁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乡加入相亲大军。此时李建国发现,与7年前已经不同,这两三年间在农村找个媳妇已非易事。
经过3年“几十次”相亲,27岁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女神”。 比李建国小两岁的妹妹如今已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了。“现在我找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女的。”他强调,“只要女方不挑我,我肯定不挑女方。”
曲周县25岁的农村青年郭威,面对记者“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的问题时,一脸嗔怪地反问:“现在还能轮到男方挑?”
这两年,冀南农村的女青年可谓“不愁嫁”。“今天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明天就有小伙子和媒人登门提亲!”采访中,有多位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民这样告诉记者。
媒人安排四五个小伙子依次和同一个姑娘相亲,在邢台、邯郸一带农村已是“见怪不怪”。李建国告诉记者:“我和姑娘聊了会儿,想问她要个电话号码,她却说等跟后边的小伙子都见完了再说!”对于这样的相亲,李建国坦言:“感觉像是求职面试!”
邯郸、邢台一带农村,大部分青年在外打工,每年打工青年返乡过春节时,是农村青年见面相亲高峰期。而去年腊月,郭威只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见了面;今年正月一次亲也没相到。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相亲的女孩儿!”他无奈地表示。
为什么最近两三年当地男女比例出现如此差距?
其实,“媳妇难找”早在郭威读村小时就已初露端倪。“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他回忆说,班里30多个学生中,“男生是女生的两倍还多”。
有农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是不允许生二胎的,而第一胎是女孩的还会允许生二胎。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如今农村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衡。
一名曾在鸡泽县小寨镇计生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干农活,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一查出来是闺女就做流产了,这一拨净小子。你打听吧,哪个村都是!”
对于农村 “找媳妇难”的成因,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则补充说:由于收入、房子等现实问题,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则多了在城市结婚成家的选择。
邯郸市广平县人民法院吕善平法官告诉记者,如今“找媳妇难”已导致农村一些地方早婚现象重新“抬头”。曲周县李于子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文芳也对记者证实:“在当地,男方超过25岁,就意味着找对象更难了。”
已进入“危险区”的郭威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没结婚。“一家四口人整天就为这事唉声叹气!”由于找不着媳妇,郭威家所住的村子这两三年每年仅有一两家办喜事。去年一年,30多个适龄未婚男青年仅有一人成功“脱光”。

剧中父母为了给未来儿媳凑够三斤百元面值人民币的彩礼而将钱用水浸湿。这来自时下冀南农村一些地方索要“新三金”彩礼的现实。《恐婚时代2》剧照
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事,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冀南农村青年婚恋现状调查
有2000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22~26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30人;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2000人,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30多人……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却寥寥无几。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邯郸曲周、鸡泽、广平、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找媳妇难”已成为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
曲周县李于子口一位40多岁的热心妇女告诉记者,临近各村以至临近各县都是如此——这两年每个村都有20多个找不着对象的小伙子,“条件还都不差”。
冀南农村普遍出现的“找媳妇难”,已不仅仅是让父母和本人头疼的“家务事”。
有鸡泽县赵庄村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开会就为这事发愁!”而当一位鸡泽县的妇女向曲周县的朋友打听是否有适龄姑娘的信息时,这位朋友立刻笑着“警告”她:“你可不能挖我们村的墙角啊!”
有媒体报道,隆尧县更有村委会向所有村民承诺:只要把女儿嫁到本村,奖励2000元;只要把本村或外村的女青年介绍给本村的男青年,奖励介绍人1000元。
记者发现,由于“找媳妇难”引发的专业媒人“不择手段”谋利、女方对彩礼“狮子大张口”,以及暴露出来的农村传统婚恋观念令人堪忧。
四五个小伙子排着队跟同一个姑娘相亲
“19岁时,对于相亲找对象,感觉就和看偶像剧一样——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女神’。” 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87年出生的他“相亲史”始于19岁。
后来由于20岁外出打工,婚姻大事被暂时“搁下”。3年前,24岁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乡加入相亲大军。此时李建国发现,与7年前已经不同,这两三年间在农村找个媳妇已非易事。
经过3年“几十次”相亲,27岁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女神”。 比李建国小两岁的妹妹如今已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了。“现在我找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女的。”他强调,“只要女方不挑我,我肯定不挑女方。”
曲周县25岁的农村青年郭威,面对记者“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的问题时,一脸嗔怪地反问:“现在还能轮到男方挑?”
这两年,冀南农村的女青年可谓“不愁嫁”。“今天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明天就有小伙子和媒人登门提亲!”采访中,有多位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民这样告诉记者。
媒人安排四五个小伙子依次和同一个姑娘相亲,在邢台、邯郸一带农村已是“见怪不怪”。李建国告诉记者:“我和姑娘聊了会儿,想问她要个电话号码,她却说等跟后边的小伙子都见完了再说!”对于这样的相亲,李建国坦言:“感觉像是求职面试!”
邯郸、邢台一带农村,大部分青年在外打工,每年打工青年返乡过春节时,是农村青年见面相亲高峰期。而去年腊月,郭威只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见了面;今年正月一次亲也没相到。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相亲的女孩儿!”他无奈地表示。
为什么最近两三年当地男女比例出现如此差距?
其实,“媳妇难找”早在郭威读村小时就已初露端倪。“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他回忆说,班里30多个学生中,“男生是女生的两倍还多”。
有农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是不允许生二胎的,而第一胎是女孩的还会允许生二胎。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如今农村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衡。
一名曾在鸡泽县小寨镇计生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干农活,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一查出来是闺女就做流产了,这一拨净小子。你打听吧,哪个村都是!”
对于农村 “找媳妇难”的成因,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则补充说:由于收入、房子等现实问题,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则多了在城市结婚成家的选择。
邯郸市广平县人民法院吕善平法官告诉记者,如今“找媳妇难”已导致农村一些地方早婚现象重新“抬头”。曲周县李于子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文芳也对记者证实:“在当地,男方超过25岁,就意味着找对象更难了。”
已进入“危险区”的郭威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没结婚。“一家四口人整天就为这事唉声叹气!”由于找不着媳妇,郭威家所住的村子这两三年每年仅有一两家办喜事。去年一年,30多个适龄未婚男青年仅有一人成功“脱光”。
网络时代的农村青年,婚恋观念却停留在20年前
对于时下专业媒人组织的程式化相亲,张嘉概括为:“她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她怎么问你,你就怎么问她!”而在他并不算短的“相亲史”上,不同于这样的相亲交友,只有过一次例外。
说起前年的那次恋爱经历,张嘉认为还颇有些戏剧性。“姑娘是一天晚上我用聊天软件的‘搜索附近人’的功能,搜索出来的。”姑娘所住村庄与张家相隔三里地。
相比相亲直奔主题的程式化问答,张嘉和姑娘在互联网上的聊天可谓“天马行空”。一聊十几天后,张嘉得知姑娘还“没婆家”,于是提出“见个面”。
有了之前的充分了解,两人很快确立恋爱关系。虽然最终因为彩礼等问题,两人没能走到最后,但张嘉坦言,这才是恋爱的感觉。
记者了解到,在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村青年中,有张嘉类似经历的并不多。虽然邢台、邯郸一带农村青年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打工的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男女青年还是回乡谈婚论嫁。穿着时尚的他们在恋爱婚姻的途径、方式上和二十年前基本一样——由媒人带着相亲、订亲、结婚……
“即使是在外边谈了恋爱,一般父母的态度也是能拦住就拦住。”曲周李于子口村有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民还是觉得结婚对象是“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更踏实。
吕善平也发现,跨区域的农村婚姻,由于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为人处事上的差异,更容易引发夫妻、婆媳矛盾,离婚率较高。
于是,每年打工青年春节返乡时,各村相亲的汽车会把村子道路两边挤得满满当当。“跟赶庙会一样!”崔博说,“哪个村都这样!”
在李于子口村,记者了解到,和二十年前一样,如果相亲见面的男女感觉不错,就会一起赶个集。“就是一起到集上转一转。”有村民对记者解释,如果双方感觉还可以,男方就给女方买件衣服;如果女方感觉不行,男方给买衣服也不接受。
赶了集、买了衣服,双方接下来就会订亲。“很快!”这位村民告诉记者,从相亲到谈婚论嫁,就见个三四面。
吕善平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农村青年中的离婚率有不断提高之势。“离婚率提高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们思想意识在进步。”但这位法官同时认为,“闪婚闪离”与时下农村青年“结婚草率、离婚草率”的现状也不无关系。
去年,许海宁曾试图为农村青年男女搭建交友恋爱的网络平台,改变当地农村青年几十年不变的婚恋方式,但却以失败告终。
“当时的想法挺好。”许海宁花200元购买了相亲交友程序放在有关网站上。他还计划依托这个网络平台,再策划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野炊、春游等。
虽然在《恐婚时代1》的片尾他还为此打了广告,但这个相亲交友平台却一直人气低迷。“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害羞、不好意思,不愿参与。”他不禁感叹道,网络时代的农村青年婚恋观念为什么还依旧停留在20年前?
(本报记者 樊江涛)